一分钱的佣金
2021年的最后几天,长沙罕见地下了一场大雪,雪覆盖了路边的行道树和电动车。长沙雨花区的车站南路上,便利店老板郝大强正在清点各个社区团购平台送来的菜。
这条街上,社区团购自提点以50米一家的密度存在着,常常有人进来郝大强的店里提货,却发现查不到货号,再一核实,对方预定的自提点是隔壁的另外一家便利店。
郝大强的店里也同时开通了兴盛优选、盒马、美团优选和多多买菜。在长沙,一家便利店同时作为四五家平台的自提点,这是一种常态,是巨头争抢团长造成的局面。2019年底,各个社区团购平台的城市拓展人员活跃在街上,反反复复扫街,不放过任何一个便利店,每个团长都听过上门的拓展人员说过这样的话:“要不要开一个新的团?赚一份钱也是赚,赚四份钱也是赚。”
作为社区团购的最小单元,自提点密密麻麻在地图上蔓延开来是这门生意走向狂热的最直接证据。在湖南郴州,十荟团的自提点一度达到4000多个,长沙最大的小区湘江世纪城里,美团买菜和兴盛优选的自提点有20多个,橙心优选有90多个,多多买菜的自提点则更多。那时候巨头们相信“得团长者得天下”,团长拉新用户的佣金从10个点涨到12个点,后来又涨到15个点。
有一段时间,团长们确实赚到了一些钱,那是社区团购各个平台大打价格战的时候,人们对社区团购这个新事物充满了热情。湖南常德澧县的团长李梅记得,2020年年末的时候,冲着秒杀活动来的用户一过夜里十二点就疯狂下单,手机的提示音吵得她睡不了觉。
程若春曾经是零点秒杀大军里的一员,这位在县城独居的中年妇女在刚接触到社区团购的时候,对逛和买兴致勃勃,她和邻居姊妹一起加了六个群,附近的团长每天会在群里扔秒杀链接,她们就一起抢当天的一分钱货品。闲暇时候她自己也逛,几毛钱几块钱的东西遍地都是,什么都忍不住加购物车。
靠便宜吸引大量新用户涌入,带来飞速增长的单量,这些单量又支撑起庞大的供应链、物流配送和末端的团长体系。“烧钱扩张”,社区团购平台们曾经试图用这种以前在外卖、打车等互联网领域百试不爽的办法,改造规模数万亿的传统社区零售生意,以规模和效率降低成本,最终实现盈利。
但眼下,所有人都能感觉到,单量在下降。这个元旦,李梅打开几个平台的后台看了眼这天的单量,有个平台只有3单。长沙本地的零食供应商素芳关注到,在兴盛优选上,一些产品的单日售出量下降到了几百份,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以前都是上万单的”。最近半年,平台上的单品数量(SKU)也在减少,从几千个减到几百个甚至几十个。
单量降下来,团长们的佣金也跟着减少。郝大强不再像以前那样把全部精力投到社区团购里了,2020年4月开团那会儿,他和这条街上的团长们暗暗较劲,为了争抢附近的小区居民,大家都在拉新建群的游戏里鼓足干劲,自己备了成箱成箱的盐,下单就送小礼品。
对社区团购的热情褪去后,团长们的怨气渐渐显露出来。多多买菜送来的两大袋菜需要团长自己分装,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郝大强用店里的塑料袋打包完菜,讲起一年前多多买菜的推广人员进门时,承诺过会给团长补贴塑料袋,火气一下子上来了,“半个袋子都没看见过”。李梅说,一个最小号的塑料袋的批发价是7分钱,“每天都在给多多买菜贴袋子”。
社区团购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遇冷,但亏损的财报和接连不断崩盘的创业公司离团长们太远,这些位于行业最末端的团长们只能隐隐约约感受到一些变化,比如起初与团长们联系的BD(商务拓展)早已辞职,对接人换了好几拨。
敷衍也开始体现在明面上,有一天对货的时候,李梅突然发现,以前的清货单上会显示每份商品的价格和团长对应的佣金,但这些不知道何时已经被隐去了。她也没有精力再追究,“就这样吧,也只能继续开着”。最近,她甚至拿过一分钱的佣金,“毕竟没有再小的数字了,总不能给我半分钱吧”。

▲长沙街边随处可见的社区团购海报。
熬一熬,就能好?
社区团购对于便利店店主们来说,本来就是一个副业,无非赚多或者赚少,赚不了钱就不干了。但越往上游走,对这个行业的冷意感受得越真切。
从2021年9月开始,湖南永州的张春丽看着自己一点点建起来的仓库,无数次想要关停它,又无数次想象也许下个月一切就会回到正轨。张春丽经营着一个网格仓,这是社区团购中物流配送的一环,平台向供应商订购的货品先运送到中心仓,再分发至散落各区的网格仓,再送到团长们的自提点,最后由客户自己取走。
网格仓的概念兴盛于社区团购最狂热的时候,激烈的价格战、层出不穷的“一分钱”优惠活动,和高价争夺团长、抢占地盘,只是这场战争的前奏,随之而来的是供应商和仓库不断扩大的产能,以及数量不断增长的司机和分拣员。
张春丽的网格仓为十荟团服务,这家2018年发源于湖南的社区团购平台曾经和兴盛优选、同程生活一起被称作社区团购“老三团”。但在2021年夏末,十荟团毫无征兆地出现了裂隙,8月20日开始,十荟团被爆出大量裁员,长春、南宁、青岛、漳州、福州、哈尔冰等城市的供应商陆续接到当地网格仓即将关停业务的通知。
永州位于湖南的最南端,隔壁广西关站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这里,人们开始不信任十荟团。有人问张春丽:“你们不会也发不了货吧?”她回应说:“我是永州人,我不会跑的,要是有一天交了钱不发货,你们可以来我家找我。”
尽管十荟团内部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只是部分亏损较高的区域将逐步关停,湖南、湖北、江西等优势区域会保留下来,但这无法给人信心。颓势在蔓延,9月以后,十荟团在湖南的部分地方网格仓的订单数量从峰值时候的一万多单回落到五千多、两千多单,进入年末的这几个月,张春丽甚至能看到刺眼的三位数订单。
单量回落之后,随即而来的是亏损和被拖延的工资。张春丽9月的司机工资延迟了一个月,她跑到十荟团在长沙的办公室,赖着不走睡了两天,工资才发下来。紧接着,10月的工资也拖着不发。
十荟团的管理层总有新的理由,有时候是“美金兑换成人民币需要时间”,有时候用盖公章的承诺书打发她。但每一次,公司的回应都是“会好的,账面上还有钱,我们大家就齐心协力熬一熬,会过去的”。事实上,一直到后来十荟团办公区域撤走,与她对接的管理层还坚持称,马上会有新的融资下来,再等一等,工资很快能发上。
在此前的招人过程里,为了招到及时所需的司机,几乎所有的地方网格仓都选择承诺给司机保底工资,张春丽给手底下的司机开6500元一个月。没有那么多订单之后,配送的司机闲了下来,每个司机手上只剩下一百多单,工资成本却成了一个极大的负担,张春丽不得已裁了两个司机。她原本想遣散更多司机,但要完成履约,在11点前将货物送到几十公里外的乡镇里去,还得留一些人。更重要的是,所有人都告诉他,这是淡季,将来订单再上来了,再招司机不容易。
张春丽曾在微信群里提过要关停网格仓的事情,但手底下的司机也不想失业,小城市里本来工作机会就不多,过年前背井离乡去打工无疑是困苦的,司机们反过来都劝她再熬一熬,“起码把年过完”“做生意都有一个困难期,说不定熬一熬就过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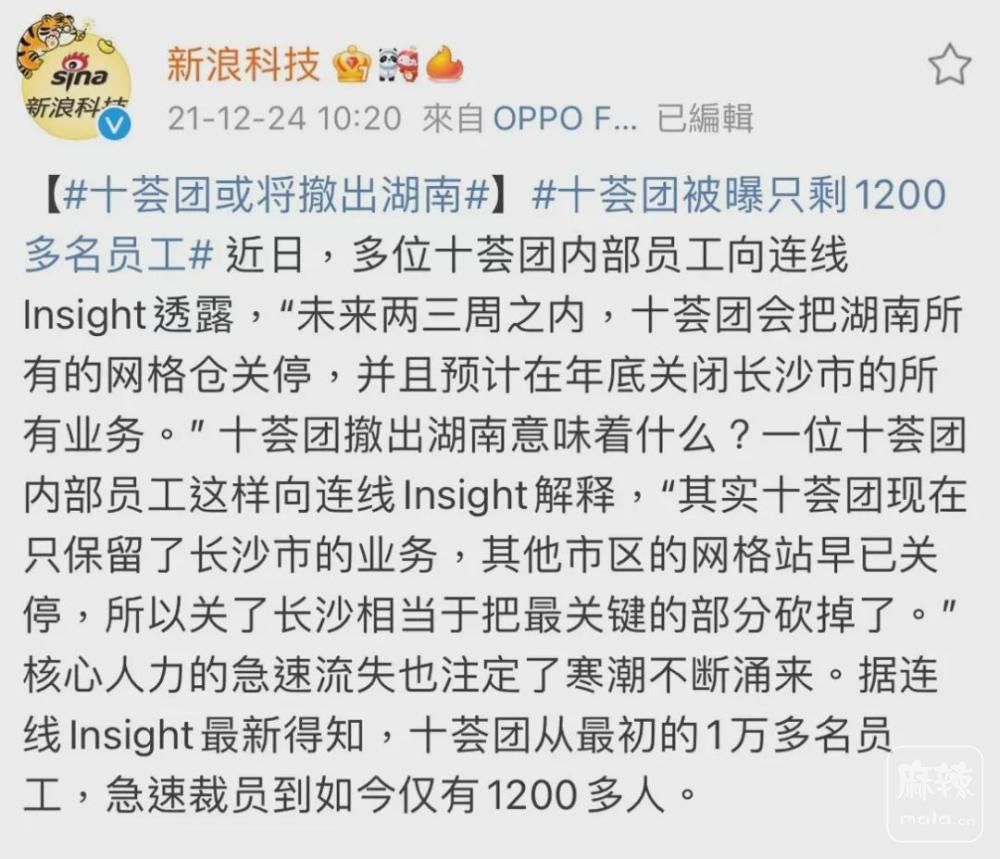
▲2021年底时,十荟团传出“撤出湖南”的消息。图/手机截图
不缺钱,就缺单量
裁员、关仓的新闻传到地方网格仓的时候,网格仓的站长和司机们不是没有怀疑过。但大多数曾经被印着“阿里巴巴十荟团”字样的海报吸引而来的普通劳动者们选择朴素地相信,“那么大的公司,不会说倒就倒的”。
更现实的一面是,持续投入的成本让人很难果断及时脱身。“人一旦一只脚踏入了这里,享受到了甜头,就很难再主动选择退出。”
社区团购最火热的那段时间,大量的网格仓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搭建起来。张春丽决定开始做十荟团网格仓的时候,一个做物流的朋友带她去找仓库,当天就把合同定了下来,第二天货就从长沙发来了。第一天送完货之后,她才有空去采购托架、菜筐之类的物资。她还买了一台专门送菜的面包车,却连提车的时间都没有,上牌选号都是销售帮忙完成的,最后也是销售帮忙把车开到仓库才完成了交付。
价格战越打越激烈,带来暴涨的单量,在永州这个湖南省南部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小城市,网格仓数量一度达到40多个。为了跟上单量,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一些网格仓甚至升级过五次,有时候是因为面积,有时候是要做冷库,有时候是需要恒温仓。
张春丽的仓库也升级过三次,她最早找到的仓库只是一个很普通的门面,单量上涨,送过来的货物堆到门口,她又花了三四万在门口搭了一个棚。再后来,仓库面积一路扩张到现在的1000多平方米。
那时候的繁荣,让人完全想不到有一天竟然发不出工资,大家想的是上市、分钱。海报以千张为单位运往各个市区和乡镇的网格仓,上面永远印着好消息,比如十荟团拿到了7.5亿美元的投资。每一个网格仓的人都听过这样的话:“十荟团是要上市的,上市了你们作为老员工是可以买原始股的。”
在永州,一些末端网格仓的司机数量在短时间内从六七个涨到二十几个,夏天的时候,这个数字超过了六十。司机们通常凌晨三点上班,等送完所有的货,就到了下午四五点,一个月忙下来,能挣五六千块钱。
很长一段时间里,工资不是问题,补贴不是问题,这个行业可能有很多问题,但唯一不缺的就是钱。同程生活自2018年成立起,八轮融资总额高达19亿人民币;兴盛优选的D轮融资达到了30亿美元;美团2021年第二季度在社区团购为主的新业务部分烧掉了92亿人民币。巨头互联网公司要么亲自下场,要么投资“老三团”打代理人战争,各个都是不缺钱的主儿。
“不缺钱”让社区团购整个行业像一个气球一样,猛烈地膨胀壮大,系统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为持久的战争做准备,充足的弹药是持久战的底气,只要能攻城掠地,把对手挤死,钱就烧得值。
所有人都以为这个行业迎来了最好的时候,并将持续好下去。尽管当时摆在巨头和创业公司面前的是一场不知道终点的混战,但每一个企业定下的目标都很宏大:兴盛优选的目标是日单量2000万,美团优选定下过年目标1亿日单量,多多买菜的高层定下1500亿年GMV。
单量!单量!这是唯一的KPI,有好看的单量数据,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钱,这些钱从源头流向下游,流入网格仓主、团长和消费者的口袋,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这个链条,想在风口上大赚一笔。

▲湖北宜昌,商家在门店前张贴的十荟团海报。图/视觉中国
赔本的生意
2020年整个年底,供应商素芳都在不同的会场之间流转。那段时间,以社区团购为主题的行业研讨会密集出现。2020年11月,她特地穿了一身绿色的旗袍去了开曼社区团购大会,还上台做了分享,紧接着还有社区团购供应链俱乐部私董会,半个月之后又是社区电商创新大会,她跑去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参加,现场所有的位置都坐满了,涌进来的参会者甚至站着挤满了通道。
巨头来临的消息最早传出来的时候。素芳曾经翘首以盼过,她以为,在未来,这些都将是自己的客户。她上赶着想跟对方对接产品,却发现对方“唯一的需求就是便宜”。巨头的钱像空气一样源源不断地注入,各个平台定价的逻辑从“少挣一点”到“不挣钱”,再到甘愿“贴钱”。

▲素芳的办公室里,摆着一张湖南地图,这是社区团购开始之后的习惯,方便随时给外地客户讲湖南各区县的地理位置。
价格战打得最火热的时候,社区平台上的商品零售价格一度低于本地市场的批发价。拿箱装12罐310ml王老吉来说,原本市场上给便利店的进价是29元,但在社区团购平台上,一箱只卖27元,由于补贴之后的价格过低,社区团购平台一度成为便利店和小超市的进货渠道。一些产品的成交量和流转率被拔高到一个夸张的数字。供应商把红牛等商品当硬通货囤着,从平台上大量买入,转手又供应给平台,来回能赚两波差价。
在一切以单量为导向的体系里,很难说清楚这些暴涨的单量掺杂了多少水分。网格仓站长梁爽在郴州招来的40多个司机要配送2000多个自提点,不同的平台对配送时间都有比较严格的要求,但是有些隐藏在居民楼里的配送点,让司机花很多时间去找,有时要送上30多层,滑稽的是,这些居民楼里的自提点通常只有一单,是自提点的老板自己买的菜。
在巨头们疯狂招揽团长的时候,商超老板不够用了,一些普通小区的居民也加入到团长的行列里,对于他们来说,反正自己每天要买菜,把家里设成自提点,就会有司机送货上门,自己还能抽到一点微薄的佣金。为了比拼配送效率,平台只能招更多的司机,这进一步提高了履约成本,让这门生意更不赚钱。
社区团购平台们乐见被“薅羊毛”,以滴滴、美团的案例看,前期的亏损能培育用户的使用习惯,提高市场占有率,最终通过涨价把亏掉的钱赚回来。但这样“催熟”市场的行为很快就被叫停了,监管部门在2020年底发布了“九不得”政策,意图抑制社区团购以排挤竞争对手或独占市场为目的的低价倾销、价格串通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也限制了后期通过收购、并购等实施垄断的途径。3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又正式依法对橙心优选、多多买菜、美团优选、十荟团等所属的四家社区团购企业分别处以1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食享会被罚50万元。
监管的影响是缓慢展现的,尽管再难见到一分钱的货品,但相较线下实体店,从2019年就开始使用社区团购的程若春仍然感觉平台商品更划算,她提着刚买来的葡萄柚向同事“安利”,兴盛优选上的葡萄柚才3块钱一个,而同样大小的果子,小区水果店里要花8块钱。
社区团购平台仍维持着“便宜”的惯性,但风向确实是变了,在舆论环境中,押注社区团购的互联网巨头们被批评“只惦记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和小商小贩抢生意”。更现实的变化是,补贴减少后单量增长的速度开始放缓,烧钱的投入产出比下来了,用户还没有真正习惯社区团购的便利,就随着价格优势丧失而回流到街巷的菜市场和小超市里。
烧钱扩张的故事讲不下去了,社区团购一下子失去了想象力,变成了一门和二道贩子没什么区别的普通生意,资本热潮逐渐退去。那些风光一时的创业公司们突然发现,手里的钱开始不够用了。
十荟团的上一次融资是由阿里巴巴和DSTGlobal联合领投的7.5亿美元。每日人物连续问了多位十荟团的网格仓负责人,巨头们来临的时候,他们是否感受过一些冲击,得到的都是笃定的回答,“没有,完全没有”。一位在十荟团工作了三年的员工坦言,“那个时候的十荟团不缺钱”“什么都不怕”。但到了十荟团收缩回湖南、湖北时,连武汉也没多少供应商敢继续给十荟团供货了。
这与共享单车当时面临的挤兑多么类似,原本情况没那么遭,但大家没了信心,排队退押金成了压垮现金流的最后一根稻草。所有人都知道,“社区团购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赚钱”。
12月底十荟团倒闭跑路之后的维权现场,一位在大楼上班的女士听到吵闹的动静来围观,听说是一起社区团购公司跑路事件,她想起了自己用过的美团优选和多多买菜,唯一的印象是便宜。
她问周围的人:“十荟团这种公司靠什么赚钱啊?”
“不赚钱。”一位供应商回她。
“不赚钱,这怎么可能呢?”她显得有些过于惊讶了。
“就是不赚钱的,都是在烧钱。”
树倒猢狲散
泡沫被戳破的速度要比它膨胀起来的速度更快。
2021年7月6日,同程生活创始人何鹏宇在内部信里提到,公司将改名为“蜜橙生活”,转型批发。据晚点LatePost报道,一位后来欠款达到1000万的供应商给何鹏宇打电话,他还表示只是业务重组。
尽管自己手上也还有五万多的货款没有收回,素芳也没意识到,内部信已经是这家社区团购公司最后的挣扎了。第二天,何鹏宇宣布公司破产。素芳这才想起不久之前,一位与她要好的高管曾在微信上向她委婉透露,“公司可能不太好了,你那边还有多少货款?”她追问回去,对方没有再回复。当时她以为,不太好了也就是生意难做了一点,“那么大的盘子,不可能一下子就崩塌吧?”
再回头去看,对于社区团购来说,瞬间崩盘的事情在2021年下半年里反复上演:20天之后,食享会武汉总部也人去楼空,创始人戴山辉悄然卸任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消失在大众视野里。再接着,就是十荟团的溃败。
2022年元旦,每日人物在长沙看到了十荟团濒死挣扎后留下的一地鸡毛,讨债的供应商和网格仓员工占领了十荟团位于华坤时代的办公室,一位网格仓负责人指着大楼说,“12楼、13楼、15楼、20楼,原本都是十荟团的办公室”,但几乎一夜之间,这里就人去楼空了。管理层的办公室里还散落着一些大厂员工的面试简历没来得及收走,原本应该贴满大街小巷的海报现在被贴在了玻璃门上,防止外面的人看见里面的景象。

▲十荟团办公室,用海报封住了玻璃门。
供应商的货款没能结清,员工的工资和加班费就更不用说了。讨债的人带着“还我血汗钱”的黑白横幅出现在全国各地,现场以欠款金额和供货种类来称呼讨债的同伴,比如那个“有七万块钱没拿回来的卖鸡蛋的”“替手底下四十几个司机要钱的网格仓的”。
一位广告供应商去了北京的十荟团总部,在大使馆街区,他看见讨债的人不到五分钟就被“劝走”,他又回到长沙,依然没什么进展。原本他还打算去十荟团江西的办公室要钱,那里的区域业务还在进行,但在人群里,他认识了一位从江西跑到长沙来要债的供应商,忽然觉得去哪里希望都不大了。
“老三团”里,只有兴盛优选顽强地活了下来,但从9月开始,这家才从价格战中缓过来的公司呈现业态收缩之势:不再开通新城市,许多“预备开通”的城市业务全面暂停,一些已经租下大仓的城市也暂停拓展。兴盛优选的运营口号原本是“用户体验,拼命狂奔”,现在,这句口号的后半句变成了“降本增效,做深做透”。一位接近岳立华的兴盛优选内部人士告诉每日人物,“(岳的)目标就是不离开牌桌”。
对所有的创业型公司来说,曾经用钱砸出来的市场并不一定是安全的。一时好看的单量要用更大成本的产能全面升级来托住,前述兴盛优选的人这样总结这一切:“订单量涨上去之后,你的产能要匹配,为了匹配产能,要扩仓,扩大供应链,要保障配送速度,要招人,但你不知道这种激情什么时候会结束,订单量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所有配套的东西都不知道如何去处理。”
在永州,许多快速建成的网格仓后来的单量只有三四百单,让张春丽这样把身家投入进去的小个体户叫苦不迭。随着一个又一个头部公司的倒下,这个行业已经不需要那么多供应商,素芳将江西的仓库关停了,没有赚到钱的一年,合作伙伴将收到的货款直接卷走了。
她并非不能理解,这就是生意不好做的时候要反复面对的场景:关于讨不回来的钱,和脆弱的、随时会破裂的商业关系。一年以前,她看着人们从其他行业涌入,搞建筑的,搞培训的,不管有没有专业技能,全部进来成为了供应商,想跟巨头们合作赚钱,“原本想去淘金子的,结果只收获了一堆沙子,还不一定回得来”。
没有赢家
很难找到一种合适的情绪来概括社区团购这一年。从程度上来说,社区团购并不是这一年里败退得最惨烈的行业。踩下刹车的时候,这个行业远远没有达到顶峰。只是,围观完这个行业的狂奔与混战,余下的日子里,除了局内人,很少再有人愿意拿出同等的关注。
已经离场的创业公司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不缺钱的巨头们还在苦苦坚持,他们的日子也没有那么好过。滴滴第三季度财报透露,橙心优选亏损额达208亿;2021年起,美团优选所属的新业务板块连续亏损,前三个季度亏损额分别是80.4亿元、92.4亿元和109.1亿元;多多买菜也拖累了拼多多整体盈利的步伐。
当蛋糕不再变大,曾经亲密无间、共享红利的人之间纠缠多了起来。十荟团维权现场的供应商们纷纷否认在这个行业里赚到了钱,他们讲起巨头采购们的傲慢,和报价不得不越来越谨慎的无奈。一位鸡蛋供应商说,巨头的采购喜欢诈唬人,不仅要和别的平台比,同一个平台的不同区域之间也要比价,“长沙的已经便宜到这个程度了,内部数据里如果显示别的地方价格更低,他们就会推进其他区域的供应商进来跟我们抢生意”。
一位供应商讲起半夜补货的场景,“缺一袋鸡腿肉也要你开冷链车去送”,货物从供应商的仓库送去平台的仓库,通常是从城市一个边缘到另外一个边缘,这门需求导向的生意并不如外界想象得轻松,“送迟了要罚,送少了也要罚,货物要是存在云仓,连毛利都覆盖不了”。
网格仓的人则会吐槽“永远还不回去的框子”,公司每天从大仓发过来的水果都是用水果框装好的,清完货要把框子还回去,但公司只要没收到框子,不管是不是第三方物流的问题,框子都需要网格仓来赔。框子27块钱一个,现场所有人都赔过框子,一位网格仓负责人甚至专门买了500个框子放着,需要赔的时候就从里面拿。
梁爽则怪罪巨头们毁掉了这门生意。社区团购是他第三次创业,在此之前,他是长沙市两个行政区的菜鸟驿站负责人,社区团购的人找上门,想收买他手底下的站点和员工,他本来不看好这门生意,觉得没什么“油水”,但还是受不住邀请入了伙。最开始“不规模,但还能赚点钱”,但价格战一打起来,整个市场就乱了,他觉得十荟团倒下就是因为“烧钱烧得太猛了,没有给自己留余地,也没有给合作伙伴留余地”。
素芳重新活跃在抖音上,号召同行们早一点抽身,转型去做团批或者别的业务。谈起因为政策和商业环境等多个因素而遇冷的社区团购,她不觉得这是坏事,“要是一直火热下去,今天死掉的行业里,就会多一个社区团购”。
就像对于兴盛优选这样的创业型公司来说,打仗也并不是本意。“社区团购从一门互联网生意变成了一门纯碎的零售生意”,当有媒体惋惜地做出这样的总结的时候,前述兴盛优选人士试图纠正这句话,“我们的核心就是零售+互联网,但在过去一年里,很多人把它玩成了互联网+零售”。
至今仍有很多小规模的微信团生存在长沙的社区里,他们没有巨头一统天下的野心,只是赚点小钱,但在巨头主导下的社区团购,终究是没能实现外卖、打车那样的“规模经济”,只能一点一点熬,一分钱一分钱地降低成本,实现盈利的目标。

▲图/视觉中国
从风口跌落后
当一个公司溃败逃窜,对于张春丽们来说,除了拿不回来的钱,一同逝去的还有一份赖以生存的生计,和过去几年里自己付出的全部真心与坚持。
“就像一个孩子一样,起初赚了钱,赚到的钱又全部投入进去,你看着它像孩子一样被你抚养大,最后还是觉得很可惜。”
听闻十荟团倒下,多多买菜的人闻讯而动,一天给张春丽打好几个电话,希望全盘接下她的仓库和司机。她没有答应,眼下,她开始怀疑这个行业是不是会好下去,“万一十荟团的今天就是多多的明天呢?”
张春丽还能想起一些两年前的事情。永州人自嘲永州是五线城市,“反正比较远”,第一个愿意来这里的就是十荟团,社区团购最早出现在这个偏远的小城市时,张春丽觉得这是个好东西,方便又便宜,村子里的留守老人多,都是她帮忙一步一步教学如何买菜的,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想要买一斤土豆,都是她帮忙下单。
张春丽那时候刚生完孩子,一边在家育儿,一边做团长。她那时候想得很简单,自己要赚一点钱,不能给丈夫太大压力。2019年的时候,一个区域负责人专门请业绩好的团长吃了顿饭,在饭桌上,那位区域负责人讲了许多未来的规划,希望团长们可以去网格仓工作。
不少和张春丽同一批进入网格仓的人都提到那个夏天的炎热。仓库里只有老式吊扇,在南方的夏天起不到半点作用,汗珠顺着额头滑下来掉在地上。由于孩子太小,幼儿园不肯收,张春丽和另外一个刚生完孩子的妈妈选择把孩子背在身上,就这样不断弯腰分拣货物,孩子也跟着头朝下。由于司机不够用,她们需要自己去送货,孩子有时候被绑在副驾驶上,有时候要一手抱着骑电动车。
另外一位母亲也出现在十荟团的讨债现场,她又怀孕了,挺着7个月大的肚子跟大家四处维权,聊起那些“把命注入”给十荟团的瞬间,现场的人开玩笑,孩子应该取名叫“荟生”。
对于这个行业里的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一个行业究竟是风口还是普通生意,并不是值得关心的问题。当普通的劳动者们一起聚集在广场上拉起横幅的时候,引来了许多人围观,为了向周围人证明,十荟团的高管消失之后找上阿里巴巴这个决定并不是无理取闹,张春丽和几个供应商一遍遍地说,“当初要不是打着阿里巴巴的旗号,谁会相信十荟团啊,十荟团算什么啊”。
淘宝买菜的图标原本是十荟团的入口,她想以此证明阿里和十荟团是不能分割的。但打开了淘宝之后,这一次,却发现那个图标早就变成了淘菜菜的入口。
她也许不会知道,也许只是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对阿里巴巴来说,投资十荟团失败只是一次试错和探路。大厂会有退路,但她没有。围观的人散去了,只剩下张春丽一个人蹲在地上默默嘀咕,“这里以前明明就是我们十荟团的入口啊”。

▲十荟团办公楼已经人去楼空。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麻辣社区平台所有图文、视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麻辣社区平台所有图文、视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