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八军团风烟滚滚的岁月(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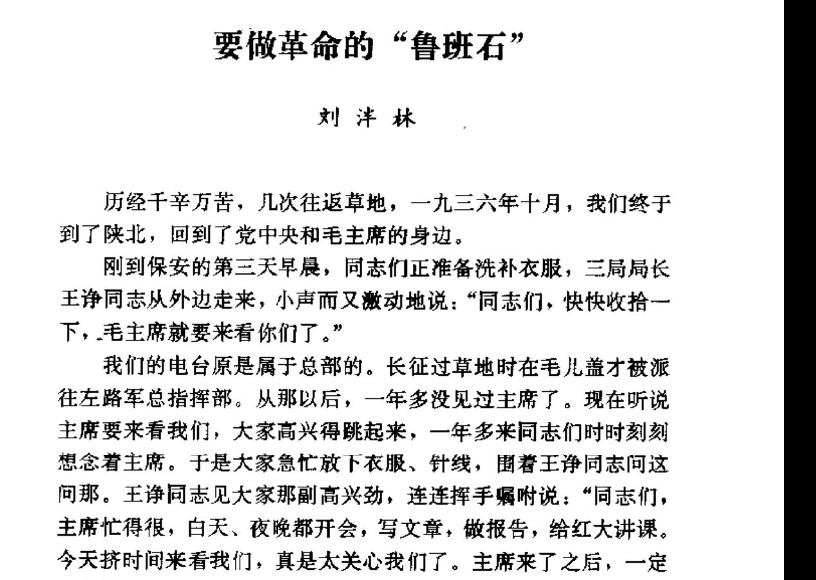
(续前)
这个空隙,我们终于冲进了岸边那一片茂盛的树林。
对岸枪声还在炒豆般的响着,我们在树林中向前奔跑。又冲出了几里路,后面的枪声渐渐停息了,我们才在一个山凹处停了下来。我抓紧时间清点了一下人员、装备,电台机器依然完好,只丢失了一付备用的双电池,可在我们的队伍中,许多熟悉的面孔不见了。我百感交集,一时竟然不知说什么才好,大家也都沉默不语,有几个同志在小心地擦拭着机器。一会儿,机器上的污泥被擦干净,可一滴滴泪水,又滴在上面。我的眼睛也湿润了,想起了刚才过江时战士们的举动,眼前清晰地出现了倒在江里的那些朝夕相伴、同甘共苦的战友们的身影……
四周的枪声渐渐沉寂下来。我看到军团直属队三三两两地赶上来。从他们的口里,我才知道,部队在江边和敌人几次拼杀,才把敌人压了下去。军团首长都参加了战斗,部队损失很大,建制也打乱了。幸好由于敌我混战在一起,敌人的飞机失去了作用,不敢贸然投弹,我们的同志才交替掩护渡过了湘江。敌人追到江边,只是隔江打了一阵枪,却没敢过江。“真险啊!” 大家不约而同地嘘了一口气。
军团首长也赶来了。我迎上去,向军团长报告了无线电队的损失情况。罗荣桓主任说:“你们电台的同志不错,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保住了电台,委实可贵,没有为革命舍生忘死的精神,是不容易做到这一点的。” 他还告诉我,部队伤亡很大,军团直属队损失也不小,政治部只跟他过来一部油印机。
入夜,我们收容好部队,在树林中露营了。可是电台的同志还在紧张地忙碌着。我们和军委的联系已经中断两天两夜了,这四十八小时的每一分钟,我们都热切地期待着军委的信息。在焦虑和盼望中,好容易摆脱了敌人的追堵,而收发报机却偏偏出了故障。几个机务员、报务员急得连晚饭都不愿吃,一直检修到深夜,还是不能使用。
我把这令人沮丧的消息报告给军团首长,心想准要吃批评了。因为我比别人更清楚,首长们这几天不仅急于得到军委的指示,而且更关心着军委的安危。结果出乎意料,几位首长听了我的报告,谁也没有批评,反而安慰我说:“不要着急,回去让同志们休息,明天再修吧。”
回到电台,我把军团首长的意见转告大家,几个人象没有听见,半天谁也不动,仍是围着收发报机这里瞧瞧,那里弄弄。是啊,电台联系不上,都感到是自己的失职,这个时候,谁肯去睡觉呢?望着同志们那一双双布满了血丝的眼睛,那一张张枯瘦的面庞,我实在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
已是下半夜了,满天的星斗在夜空中闪烁着,同志们还是毫无倦意的检修着收发报机。不行,无论如何要让大家休息一会,哪怕是睡上几个钟头也好。我板起面孔,对大家说:“现在,我命令立刻睡觉,谁也不准再干了。” 大家望着我,人人都是满脸委屈。我只好又厉声说:“执行命令,党员带头休息!” 好不容易才把大家赶走了。我合衣在充电机旁躺下,翻来覆去睡不着,一合上眼皮,几天来的险恶场面便浮现在脑际,而更令人沮丧的是两天没有和军委联络上,军委和兄弟部队到底怎么样呢?…… 想着想着,毕竟我也是困倦已极,不知什么时候,朦朦胧胧地入睡了。
一道亮光射进我的眼帘,我一翻身坐起来。啊!天亮了!这是一个大晴天,灿烂的阳光照在林中的空地上,许多同志都把昨天的湿衣服晒在草地上。一个机务员找到我,指着这些衣服说:“政委,有办法了。昨天检查收发报机的所有零件都没有毛病,准是因为过江在水里泡湿了。我们把收发报机也晒一下,说不定就能用了。”“对呀!” 围过来的几个同志兴奋地喊起来。
很快,我们把所有的器材都打开,一件一件的摆在阳光下,晒了整整一个上午,才装配起来。打开一试,果然成功了!报务员套上耳机,轻轻地敲击着电键,那清脆悦耳的 “嘀嘀达达” 的声音又响起来。同志们一片欢呼,象打了一个大胜仗。“嘘 ——” 报务员突然神气庄重地竖起了一根手指,大家立刻安静下来。收发报机传来了军委的呼号,顿时,我只觉得一股暖流涌遍了全身。“同军委联络上了!” 同志们一下沸腾了,跳跃,拍手欢呼,有的高兴得互相扭打起来,每个人的眼眶里都闪动着晶莹喜悦的泪花……
出发号响了,部队又要行动。我急冲冲地跑到军团部,向首长们报告了这一喜讯。军团长如释重负,高兴地说:“那就好了,你一到宿营地马上和军委联络。”
当天,我们军团跟着前面的队伍出发了,我望着行进的无线电队,心中油然升起了一种自豪之情。我为我们的电台自豪,为无线电队的每一个同志自豪。我们经受了种种严酷的考验,终于在殊死的搏斗中成为胜利者!
今天,我们那台染着烈士血迹的充电机,作为革命文物,骄傲的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成为这一段历史的见证。
大苗山上
嘹亮的军号声吹来了黎明,我睁开眼睛,一片金色的阳光已经在山顶上闪耀着。山谷中仍然是黑蒙蒙的,茂密的树林团团覆盖着幽深的峡谷。几天来,除了山,还是山,没有一块平地。我们一直在这样的崇山峻岭中行进。
过湘江以后,我们红八军团先于胡岭一带负责警戒全州的桂敌。十二月六日,又奉命同红五军团扼守老山界各隘口。老山界,地图上称为越城岭,耸立在湘江西岸,是湘、粤、桂边有名的五岭之一,最高峰海拔二千一百多米,上下八十余里路,所部路,也仅仅是悬崖绝壁间的羊肠小径,远远望去,象一条细长的带子,伸向山巅,坠入峡谷,曲曲弯弯隐没在丛林深处。这里地势险要,真是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军居高临下,以要道隘口为屏障,使敌人不敢轻进。第二天,我红五、八军团移驻塘洞,仍以一部扼守老山界隘口,迟滞敌人并破坏来路。完成阻击任务后,我们胜利地翻过老山界,赶上了主力。
过了老山界,山势未见平缓。路,越走越陡;山,越爬越高。前边,仍是一望无际的群峰。这里是人烟稀少的苗族聚居区,人们都叫它大苗山。一路上虽然看到过几座苗寨,但寨子里空无一人。苗族同胞素有搬迁的习惯,过去我就听说过 “苗家搬家,苗子搬家。” 可是在反动派的欺压下,苗胞们只能向山高林深的地方躲避。大概是因为他们分不清红军与反动派的区别,听到红军来到的消息,也同往常躲避汉人一样,在山上藏身了。这些苗胞跑〔爬〕山极快,有时前卫部队看到人影,三转两转就再也找不到了。出发以来,罗荣桓主任一再强调要各单位注意做好沿途的群众工作呢。可是,在苗山上,连人影都找不到,又如何进行群众工作呢?连续的山地行军,使同志们相当疲劳,最糟糕的是粮食快吃光了。昨天晚上,司务长把保存了几天的一块猪肉拿出来,加上红薯,做了满满一大锅肉烧红薯,全队同志香甜地吃了一顿。大家吃得高兴,只有司务长在暗暗发愁,明天要是再找不到老百姓,我们就真要断粮了。
早上,我咬了咬牙,让司务长把最后的一点粮食也拿出来,煮了稀粥。这可真是名符其实的稀粥啊,除去稀稀拉拉的几把大米和切得碎碎的红薯,比清水汤稠不了多少。一些战士喝了四五碗,把肚子灌得圆圆的。不管怎样,毕竟算是吃过了早饭,队伍又继续前进了。
出发后,大家的情绪很高,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几个兴国同志还兴致勃勃地哼起兴国山歌来。看着同志们个个生龙活虎的神气,我也受到了感染。是啊!血染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之后,后面的追兵被甩得远远的,高山密林也使敌人的飞机失去了威风。眼下,同志们流露出来的胜利的情绪,不正是我们用以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力量吗!
山路,依然是那样陡峭,同志们挑着沉重的器材,一步步地往上爬着。不一会,都大汗淋漓,不停地喘着粗气,每进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气力。刚才的欢声笑语渐渐消失了。队伍前进的速度越来越慢。在一块开阔地前,我停下脚步,担心地望着正在攀登着的同志们。突然,一阵争吵声传入我的耳朵。“给我,排长。”“不,还是我挑。”“排长,我能行。”“服从命令。” 运输排刘排长声音一下严厉起来。声音消失了,刘排长挑着担子出现在我的面前。后面,一个年轻的战士噘着嘴跟上来,一见到我,那个小战士就振振有词地告起排长的状来:“政委,出发时排长讲的和我轮番挑机器。可是,到现在连担子边都不叫我碰一下,这,这合理吗?” 这小鬼委屈得几乎掉下眼泪。我看着刘排长,他只是用毛巾擦着汗津津的额头,站在那里笑着,说:“我行啊,路还长着呢。” 手里紧紧地握着扁担,扁担两头结结实实地拴着收发报机。看情形,这副担子他非要垄断不可了。一路上,运输排不知吃了多少苦,可器材却毫无损坏,只是在过湘江时掉在江里一筒双电池。为这事,刘排长自责得比谁都厉害,这是多么强烈的责任感啊。从那以后,每次行军,他都不声不响地把收发报机挑在肩上。谁都知道,这副担子是整个电台的灵魂。
对于这场争论,我没有表态,只是对刘排长说了一声 “在这里休息一下”,便匆匆拔腿向军团部走去。
昨天晚上,我就听说军团卫生部担架队要解散,这消息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夜。过湘江后,我们电台也减少不少,器材又这么多,这么笨重,如果能够给我们补充几个人,就解决大问题了。运输排减少了十来个人,沿途又无法找挑夫,实在拖得疲惫不堪,不及时采取措施,很可能不出苗山就会拖垮。同军团首长去说一下,兴许会给我们几个人,我一边走一边盘算着。到了军团部,他们也在休息。我找到黄苏政委,开口就把路上想好的理由一条条摆出来,谁知,没等我把话说完,他就发起火来:“这几个人补充战斗部队都不够,哪能给你们?告诉你,一个人也不给,如果把电台丢了,我杀你脑壳。” 这个钉子可碰得不轻,我不免有些懊丧。看到我失望的神情,罗荣桓主任笑了:“袁政委,电台的同志是很辛苦,可是,连队更需要人呀。道理我清楚的,连队多一个战士,打起仗来前线就添一份力量。和他们相比,电台再重要毕竟还不是冲锋陷阵。可是,我们的处境也实在困难。” 罗主任又说:“你们无线电队出发以来一直是军团的模范单位,领导上相信你们,你也要相信电台的同志们,只要讲明道理,我们的红军战士都能以一当十,克服任何困难的。”
罗主任的一番话,一下子使我开窍了。对呀,把困难摆到大家面前,群策群力,依靠大家来想办法,一定能把电台运出苗山。
回到电台休息的地方,我把干部召集起来开会,让大家出谋划策。运输长沉默了一会,认真考虑着眼前的问题,运输排长第一个打破了沉默:“电台是同志们用生命换来的。我们排人虽然少了,但是我们要一个人挑两个人的担子,就是爬,也要把器材带走。” 靳子云同志接着说:“运输排是最吃力的,现在应该集中全部人力保证运输排的任务。” 他的建议,得到了监护排的赞同。很快,大家就形成了一致的意见:抽调人员加强运输排的力量,号召党、团员带头克服困难。这时,司务长又提出来粮食问题,这一下,刚才兴奋的情绪又低落下来。是的,两天来,一到休息的地方,司务长就带头到处设法搞粮食,可是,没有找到苗族群众,有时路旁的粮食也被前面的部队吃光了,有钱买不到粮食,我看,粮食问题必须赶快解决。队伍出发前,先派几个人到前面去搞粮食,搞不到别的,搞些红薯也好;来不及蒸,就吃生的,搞到粮食就在路旁等候部队。” 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才使我发觉,罗荣桓同志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我们身边。他的意见,立刻得到大家拥护。开完会,司务长就带着几个炊事员提前出发了。
队伍整装出发时,我又一次做了动员,提出了 “人在器材在” 的要求。在党、团员带动下,同志们纷纷要求参加运输排的工作,个个争先恐后,这么一来,倒让刘排长作难了。
当一切准备就绪,部队就要出发的时候,一向话不多的通信员小赖突然拉住我:“政委,我也要当个运输员,为电台贡献力量。” 这个小鬼身体瘦小,怎么挑得动机器?我没有理他。他见我没有答应,更着急了:“政委,别看我个子不高,可是在山里长大的,爬山可是个行家!再说,我也要向党、团员同志学习呀!” 望着他那满含期望的目光,我只好点了点头。他立刻一跳老高,敬个礼,转身就跑。“回来!” 我喊住他:“到排里要服从领导,不许逞能。” 他笑了笑,答道:“是!” 还有,把你的枪和挎包留下来。” 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政委,你的担子够重的,我不能再给你增加负担。” 说着,一溜烟地追赶队伍去了。望着他那一蹦一跳的身影,我心里热乎乎的,有这样的战士,还有什么困难不被踩在我们的脚下呢?
中午,我们开始向顶峰攀登。面前是高耸入云的峭壁,抬头看去,帽子险些掉下,再向上只能在嶙峋的怪石间择路而攀。同志们早已饥肠辘辘,全凭着顽强的意志,一寸寸地向上攀登。大家把勒紧裤带省下来最后一点应急干粮,这时都集中起来,让挑器材的同志添一点力量;有的同志甚至把脚上穿的草鞋脱下来送给打赤脚的运输员。为了保证器材的安全,每个运输员的身后都有一、两个同志当 “保险”。山路崎岖,大家就把器材捆在背上,有的则紧紧搂抱在怀里,犹如母亲照料襁褓一样。有一个同志实在走不动了,就背着器材一点一点往上爬,直到昏过去,仍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我们的这些运输员,真是个个都称得起英雄好汉。
正是凭着这种团结友爱和一往无前的精神,我们胜利地越过了山顶。站在山顶上,象是上了蓝天,一片片白云在脚下飘过,绵延西向的群峰在眼前起伏,胜利的欢慰犹如林海涛声,激荡在我们心中。饥饿和疲劳连同这八十里大山一道,被红军战士战胜了。
下山路上,两个炊事员已经等在路旁,一大箩筐的红薯放在身边。这真是雪中送炭呀。同志们美美地吃了一顿生红薯,啊!又甜又酸,既解饿,又解渴。我问这两个炊事员从哪里搞来这么多红薯?他们兴致勃勃地讲起来:昨天夜里,前面部队驻在山下的一个苗寨。深夜,寨里突然四处起火,我们的同志在救火时抓住了三个冒充红军放火的家伙,一审问,原来是敌人派来搞鬼的,他们妄图把放火的罪责嫁祸给红军,却被警惕的红军战士抓住了。于是,我们的同志连夜在村里召集苗族同胞,让这三个放火者自己向大家交代了敌人的阴谋。反动派的罪行和红军奋不顾身救火的生动事迹教育了苗族群众,红军又送给了全寨受灾的苗胞许多白洋。这一来,苗族群众把红军当成了救命恩人,纷纷把藏起来的粮食拿了出来,一些青年还要求跟着红军打反动派,我们的司务长赶到那里,几乎没有费劲就买到了不少粮食,还找到了挑夫。…… 两个炊事员绘声绘色地述说,把大家都吸引了过来。愚笨的敌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竟然帮助红军把群众动员起来了,这真是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不知是谁喊了起来:“走啊,下山吃大米饭喽!” 队伍欢笑着向山下跑去。
下了山,天已经黑了,到处升起了炊烟。这情形,使我想起了三天前在老山界上的一件事。那天,我们翻过山顶以后,部队休息了。我看到路旁的地上堆了几块石头,上面架着一只茶缸,旁边有一位同志正跪在地上用双手拣着干草,填在石块中间,又划了一根火柴,引燃了柴草。借着火光,我发现这位同志原来就是刘少奇同志。他当时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长征时跟随我们八军团行动。过去,他曾到电台讲过几次话,我们对他很熟悉了:“首长,你为什么不叫警卫员帮你弄呢?” 他站起身来,拍了拍手上的泥土,微笑着说:“这点事情我会做也能走,为什么一定要别人来做呢?你看,” 他又说,“你看,这不是很容易吗?到处都是干柴,有一点火种就可以点燃。毛主席不是讲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少奇同志的话,象是在我心中燃起了一团火。我激动地向他敬了一个礼:“首长,请你放心,我们的同志一定会战胜一切困难,成为革命的火种。” 少奇同志信任地点着头,紧紧地同我握了手。夜幕中,那一堆堆耀眼的篝火在我眼前跳动着,把苗岭映得通红。我们红军不正是革命的火种吗?这火种是任何反动派也无法扑灭的,迟早有一天,革命的烈火一定会冲天而起,烧遍整个中国。
(原载《风烟滚滚的岁月》第 103—124 页,
战士出版社,1982 年 5 月第 1 版)
注释
红八军团:1934 年 9 月组建的红军军团,在湘江战役中遭受重创,后余部并入红五军团。
罗荣桓: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时任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新中国开国元帅之一,以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著称。
黄苏:红八军团政委,长征途中率部浴血奋战,1935 年在战斗中牺牲。
老山界(越城岭):红军长征中翻越的第一座险峻高山,位于湘桂边境,地势陡峭,是五岭山脉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苗山:今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一带,苗族聚居区。红军在此严格执行民族政策,通过救火、揭露敌人阴谋赢得了苗族群众的信任与支持。
《风烟滚滚的岁月》:作者袁光(红八军团无线电队政委)的长征回忆录,真实记录了红八军团在湘江战役及后续行军中的战斗与生活。
刘少奇: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长征期间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红八军团行动,强调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的革命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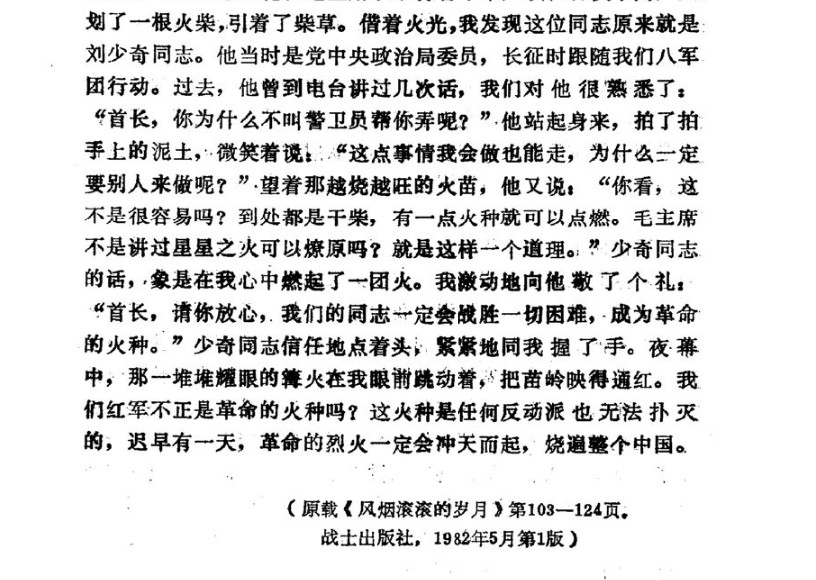
要不要我帮你整理一份红八军团长征大事记,把这段文字里的关键时间、地点和事件串起来,方便你系统了解这段历史?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麻辣社区平台所有图文、视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麻辣社区平台所有图文、视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