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 雨 (图片来源:网络)
深夜,突然被响雷惊醒,雷声就在屋顶炸响。正不知所措,刺眼的寒光在黑暗中划过,紧接着又是一声巨响。沉寂了一阵,像是在天边,又咕哝着、翻滚着沉闷憋屈的声音。我知道,更大的惊雷又在酝酿。 果然,很快第二波惊雷又炸裂了。千万只箭镞直射下来,雨点粗暴地敲打在屋顶、地面、树上和窗户玻璃上,发出沉闷的、尖细的、金属的、鼙鼓的声音,然后,汇集在一起,像千军万马,从四面呼啸狂奔而来。瞬间,密集的雨声响成一片。雨神和雷公在尽情地肆虐,向每个角落发泄。整个宇宙都成了暴雨的世界。本来就有失眠的毛病,这下,更别睡了。瞪大眼睛,木然地看着天花板,无奈地接受耳边的一切,和暴雨僵持着,等待着。不一会,先是雷公输了,最后雨神也输了,就那么一阵,来得快,走得也快。雨渐渐小了下来。 细雨在窗口那棵大银杏树上,滴嗒下来,再落到窗棚上,叮咚作响。渐渐地变成了“啪嗒、啪嗒”,节奏感很强的声音,这儿一下,那儿一下地敲着。和跌落在芭蕉上,或荷叶上的声音,有同工异曲之妙。像是在安抚,在宽慰,是那么温柔,那么动听。使人联想,使人怀旧。 “听雨”,是件雅事(不是去听暴雨呵)。过去文人墨客,常常在雨天雅集,推窗眺望细雨霏霏的江南,即兴赋诗;当然,也有怒发冲冠的儒将,眼望潇潇细雨,破碎山河,抒发直捣黄龙的情怀;也有骑着毛驴,浑身酒气,冒着沾衣欲湿的细雨,过关入川的诗人;而今人戴望舒在悠长寂寥的雨巷徘徊,就是想去会会忧怨的、气息如同丁香的姑娘。 我本俗人一个,没有什么雅兴,与这些都不沾边。 余光中有一句话“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我想,他说的应该是细雨。今夜,静静地躺在故乡的怀中,听着不紧不慢,不温不火的细雨。有点像儿时,小病在床,母亲端着汤药,娓娓劝说我喝药的感觉。又让我记起,毕业时,在成都人民公园,细雨中,两人共撑一把雨伞,依依惜别,她的对我的万千嘱咐。流落在外,我不止一次,独自撑着雨伞,在荷塘边漫步,在蕉叶下踯躅,就是想听听细雨的声音,找回当年的感觉。而今,老母早已作古,老妻是否还记得当年? 人生多少个夜晚?多少场风雨?很少有昨夜的雨声,教我想得这么久,这么远。为了生计,远走他乡,几十年风风雨雨,一事无成。而今,落叶归根,蜗居茅舍。听着窗雨,南宋蒋捷的词《虞美人》“听雨”,又渐渐明晰起来: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应该说:我比蒋捷幸运,他是亡国词人,我是盛世布衣;他少年就混迹于歌楼,我少年就为衣食奔波。我与他都曾有过青春的张扬与激情,中年流落与困顿。看惯了悲欢离合、经历了宠辱沉浮。人生况味,尽在蒋捷的“听雨”之中。 是蒋捷的词意契合我此时的心境吧?还是我在孤独中触景怀旧? 人到暮年,回忆是一支拐杖,支撑着兴致不高的精神和简简单单的生活,使人不会孤独,继续蹒跚前行。而细雨是回忆的诱因,联想的催化剂。在百无聊奈时,听听耳边亲切温柔地“滴答”声,过往的美好便一一显现。所以我喜欢听雨。 初秋,更深人静,我独自享受着“滴答,滴答”的天籁之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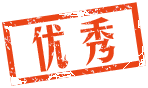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麻辣社区平台所有图文、视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麻辣社区平台所有图文、视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当前版块2016年12月1日之前所发主题贴不支持回复!详情请点击此处>>
当前版块2016年12月1日之前所发主题贴不支持回复!详情请点击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