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曾先后担任过陕西省“省长”(省主席)、北平(即北京)市长的国民党高官熊斌,在1925年11月赴苏联进行考察时就曾预言苏联“断难永久立国于世界”,详情见下面这篇文章:
熊斌其人[转载]
转自著名的杂志型丛书《老照片》的第56辑:http://www.lzp1996.com/wqyd/20091102/100.html
民国人物熊斌,军界科班出身,西北军冯玉祥的参谋长。冯氏失势后,为蒋介石延揽,
成为蒋的参谋总部重要幕僚。其间两度出任地方行政长官。(此即指其出任过陕西省主席和北平市长。——楼主点评)
近现代史中的中日“塘沽协定”,蒋选石指定代表中方谈判和签约的就是艄斌。其时,日本侵占我东北诸省,进追华北,兵临北平城下。双方各自出于争取喘息时间的战略考虑,暂作妥协。协定规定在长城以南设置非武装地带,两军各停留在此地带南北。“塘沽协定”虽使日军停止进攻,保住平津,但它默认日占东北及察北、冀东的既成事实,因而是屈辱性的,为国人诟病。熊斌回忆谈判的感受:“
战败谋和,敌方盛气凌人,于委曲中须求完成使命,此中滋味,实不堪回首。”
在今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陈设有台儿庄战役中的一份作战计划,系出于熊斌手笔。台儿庄战役歼敌二万余人,是全面抗战后我军取得的重大胜利。熊斌时任军令部次长,在蒋召开的中央军事会议上,意见纷纭,熊斌与另一位军令部次长林蔚力主一战,为蒋采纳。会后林蔚赴前线协助李宗仁指挥,熊斌则在武汉总部坐镇,发布作战命令,统筹进退。
熊斌的国家民族意识强烈。抗战时,登华山题诗云:“登太华之巅,看河山光复。”早年
在冯玉祥军中,苏联顾问要参加参谋处办公,“余坚决反对,以军令机构不容
外籍人员干预”。后
冯派熊赴苏考察,他敏锐地觉察到:“每欲至乡村看人民生活状况,招待员总婉词拖延。一般平民衣履不整,愁眉不展,市内乞丐甚多,配给食物处排班守候如长蛇阵。
其政府高级人员则享受极优,且多有外室,阶级显然。与之交涉公事,则多喜推诿拖延。”因此判断:
“彼邦政治表面上虽似有成就,实际对人民控制极严,毫无自由可言,生活甚苦;
对外不讲诚信,断难永久立国于世界。”(对外进行欺骗性的宣传,宣传其人民生活象蜜一样甜,是其“对外不讲诚信”的一个重要表现。——楼主点评)
熊斌幼习旧学,受传统道德熏陶甚深。其治军为政,崇尚爱恤民力和清廉,以“戎马书生”自许。
他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驻陕的胡宗南部队举办“总校阅”,规定农民自制棉军服,自备刀矛,远途跋涉赴会,校阅时间定在上午9时,而6时即须动身。
熊认为:“扰民实嫌太甚。”一次,胡的部队筑工事,熊以不必要而加削简。“工事木料须从山区采伐,肩负而来,
浪费民力,何忍出此”。“虽因此得罪于军方,亦在所不顾也。另一次,蒋介石听苏联顾问意见,要挖沟防日本坦克,熊复电:“如黄河天险,尚不能阻敌,则改变地形,亦属徒劳之举。且麦苗正旺,毁弃可惜……”最终他拒不执行。是年夏间,河南大旱,饿殍载途,虽陕无余粮,本救贫恤邻,余不顾军方及地方士绅反对,准杂粮百余万石出关救济,全活不少。”
他离陕返渝任新职,不住旅馆,迁入友人寓所。何成濬在日记中感叹:“哲明主陕省政三年,不贪非分之财,
甫离职亦须如此节省,其无余钱可知。今时做省主席如哲明者,真可谓凤毛麟角矣。”抗战胜利之后,熊斌
出任北平市长,仍秉故衷。日人中有以汽车、冰箱呈献者,一无所取。时人对于接收人员有‘五子登科’之讥(女子、房子、车子、金子、银子),余问之无愧也”。
熊斌任职北平市长,励精图治,“期以民主政治之精神,树立地方自治之基石”。但仅一年余,在1946年底被免职,以五十岁之壮年,即淡出政坛。个中原因,在他的自述和他人叙述的材料里没有说得很清楚。以我分析,应是他和最高当局在政策上出现分歧。熊在抗战胜利时,被任为“华北宣抚使”,利用他出身西北军的关系,成功地为蒋收编华北伪军四十余万人。但收编后,当局却不发军饷。时任军政部长的陈诚称:“此批汉奸部队何足重视;共产党未必要他们。即使投共,我们可以一次合并解决、省却许多麻烦也。”熊斌对此自是耿耿于怀。伪军遂改投中共一方。后来,熊斌在赋闲时被问及“神州变色”的原因时,亦举出“伪军未能作适当之安置”为其中“荦荦大者”之一。而熊斌虽为军人,但不崇武;曾上书蒋介石,建言“收复人心,倡造大同”,在告北平市民书中宣扬“立德”;这种思路与如陈诚所持以武力睥睨一切格格不入。国民党当局固不用熊斌,熊斌后来亦不愿入伙。1947年夏,即全国内战开打之时,乡人曾劝熊出任本县国大代表,熊“当婉拒之,盖已有国事不可为之感矣!”1948年后,熊避居台湾,解职除役,“还我自由”,寓乡间以终。……(后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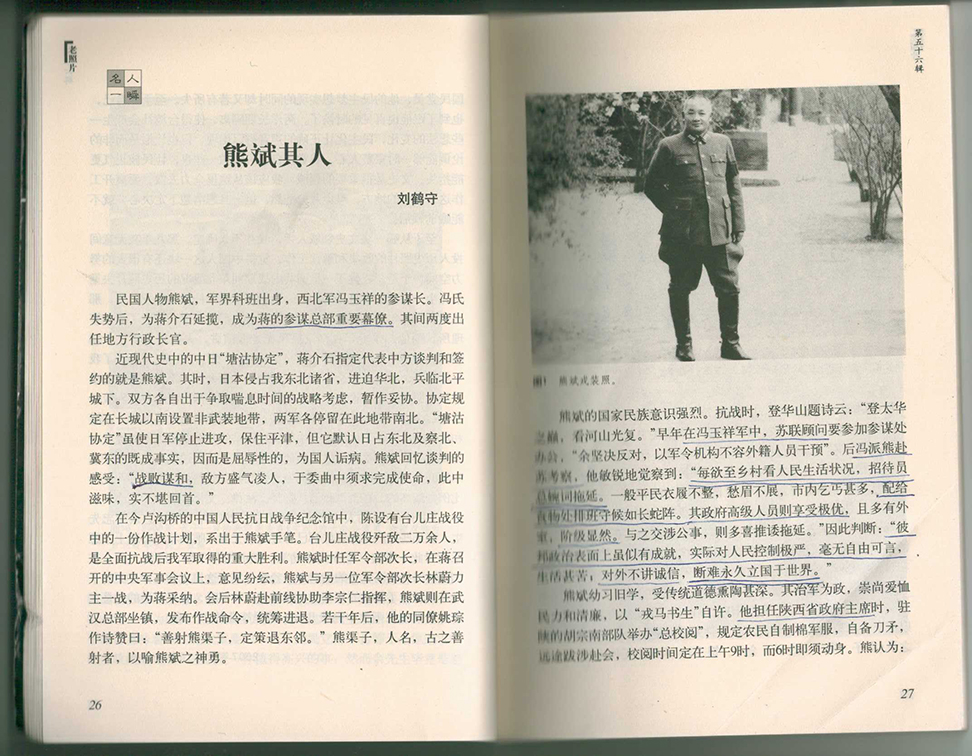 1921年徐志摩写 书评:苏联模式终会崩溃[转载]
1921年徐志摩写 书评:苏联模式终会崩溃[转载]
转自
凤凰卫视的官网“凤凰网”读书
频道如下这个地址的页面:
http://book.ifeng.com/shuhua/detail_2008_11/22/338367_0.shtml
为何徐志摩对迷倒众多中国知识人的苏联有一种特别的洞穿力?这还要看他的留学背景和所汲取的思想
徐志摩的别样见解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社会对当时苏联的看法,其实是一种考量,它考量着每一个关注中国命运的知识人的观念与眼光。那个年代,弥布着一种激越的“向左转”的氛围,因而知识人包括青年对苏联的认肯在当时不仅是多数,也是主流。……(中略)
那时,有过这样一幅英国漫画,是讽刺苏联的。画幅上“画着用纸版剪成的工厂、学校、育儿院等等,竖在道路两边,使参观者坐着摩托车,从中间驶过”。此画的讽刺意味很明显,这一切都是表面的、假的、做给外人看的。但看过此画的鲁迅不这样看,相反他在文章中认为该画是“无耻的欺骗”。过后,鲁迅专门作文“我们不再受骗了”,批评英语世界对苏联的攻击和造谣,不但为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辩护,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价值立场和眼光。
但如果把这幅画放在徐志摩面前,他的态度会如何?事实已无可能,鲁迅作文的1932年,徐志摩已经魂归天府。然而,这个问题如果依然提出,答案也不难索解。可以肯定,徐志摩不会认为这幅画是欺骗;如果欺骗,也是画所画的那个内容。
1920年秋徐志摩到英国,结识了英国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韦尔斯。是年韦尔斯曾往苏俄游历,归来后用游记记写见闻。徐志摩读后,特意为之评论。这便是徐文中韦尔斯亲身历俄的小故事。当他去参观一所小学校时,问学生平时学不学英文,学生一齐回答:学。又问,你们最喜欢的英国文学家是谁,大家一起回答:韦尔斯。进而问,你们喜欢他的什么书,学生立即背诵韦氏著作,竟达十多种。韦尔斯很不高兴,他相信这些学生是“受治”。后来,他特意不知会苏俄接待方,独自来到一所条件比前面更好的学校,又把那些问题一 一提出,结果该校学生一概曰否。接着,韦尔斯又来到该校的藏书室,书架上没有一本自己的书。韦尔斯什么都明白了。于是,徐志摩也什么都明白了,他写道:“苏俄之招待外国名人,往往事前预备,暴长掩短,类如此也。”
为何徐志摩对迷倒众多中国知识人的苏俄有一种特别的洞穿力,这还要看他的留学背景和所汲取的思想。……(中略) 在徐志摩短暂的一生中,他最想追随、同时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是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徐志摩宁可不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也要横渡大西洋,到英国跟罗素去念书。徐志摩把罗素比为20世纪的伏尔泰,可见其“高山景行,私所仰慕”。
罗素在英国时是个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出于对苏俄价值理念的认同,1920年,他随同英国工党代表团去苏联考察。这一去不打紧,所谓乘兴去,失望回,不但没有接受其洗礼,反而把对苏联的看法写成了批评性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徐志摩不但读过此书,同样,也为它写过评论。……(后略)
徐志摩的访俄见闻[转载]
节选自《经济观察报》2013年2月18日那一期第51版上的《徐志摩为什么反对苏俄》:http://www.eeo.com.cn/2013/0206/240006.shtml
当1925年徐志摩自己亲自游历苏俄之后,跟罗素一样,徐志摩也开始反思并警惕苏俄。这自然与徐志摩在苏俄的观感有关。
进入苏俄,徐志摩首先感受到的是苏俄民众的穷困。在《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中他写道:“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愈发的明显。”这不仅是当时徐志摩的游苏观感,也是瞿秋白当时的观察,当时瞿秋白曾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访问苏俄,《饿乡纪程》就是瞿秋白这一时期在苏俄的观感。瞿秋白将苏俄称为“饿乡”,里面也确是写到了苏俄民众物质生活上的穷苦。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明明知道苏俄民众生活穷苦,瞿秋白依然一心一意学习苏俄。徐志摩看到了苏俄民众的穷苦,这不符合徐志摩对苏俄的希望,因此徐志摩不得不对苏俄持一定的保留意见。
在莫斯科,徐志摩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莫斯科的街道上有男子抱着吃奶的小孩在街道上走。这种怪现象的背后,在徐志摩看来,源于苏俄规定的“一个人不得多占一间以上的屋子”的法律。苏俄政府对民众的私有财产(尤其是房子),依法没收,然后重新分配。这里徐志摩看到的是苏俄对个人私有财产的不尊重,而这自然也会引起徐志摩的反感。
徐志摩最不能忍受的则是苏俄对书籍的查禁。徐志摩崇拜托尔斯泰,因此去拜谒托尔斯泰的女儿。从托尔斯泰的大小姐的口中,徐志摩知道,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书在苏俄都差不多绝迹了,其中有一些是被苏俄政府查禁的,原因是他们的著作代表了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对此,徐志摩写道:“假如有那么一天你想看某作者的书,算是托尔斯泰的,可是有人告诉你不但他的书再也买不到,你有了书也是再也不能看的——你的感想怎样?……假如这部分的个人自由有一天叫无形的国家威权取缔到零度以下,你的感想又怎样?”
此外,让徐志摩感到恐怖的还有苏俄革命时期的革命领袖的铁面无私与血流成河时的红色恐怖。对于革命领袖列宁,徐志摩写道:他(列宁)不承认他的思想有错误的机会;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
而对于革命时期的惨景,徐志摩也曾写道:“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人民穷苦,政府侵犯民众的私有财产,与此同时政府还查禁托尔斯泰等作家的书籍,革命领袖冷酷专断,这些就是徐志摩游历苏俄时看到的现象。而这些行为,在视个人自由为最高价值的徐志摩看来,无疑是不能接受的。
“仇俄友俄”讨论时期的徐志摩
正是有了这一次的苏俄游历,徐志摩对苏俄产生了警惕之心。而当徐志摩回国之后,正是国共合作准备北伐的时期,因此各种赞美俄国的声音出现在报刊上。徐志摩回国之后恰好主持《晨报副刊》,于是在徐志摩的主持下,知识界展开了一次“仇俄”还是“友俄”的大讨论。
首先是陈启修在《晨报》发表《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在文中,陈启修认为苏俄不是帝国主义,因为它没有侵略中国。需要指出,苏俄在这一时期之所以引起知识界的同情,还与苏俄这一时期的对华外交政策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胜国,知识界对于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普遍比较乐观,然而,在巴黎和会上,最终的事实却是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这一残酷现实使得原本对英美国家抱有很大期待的知识分子对英美国家甚为反感。而在此前后,苏俄则曾向中国发出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宣言,这不能不使中国知识界对苏俄产生好感。后来胡适在反省他对俄国的看法时,就曾说他曾一厢情愿地抱着“总希望革命后的新俄国继续维持他早年宣布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主义的立场”,然而,苏俄对华的一系列宣言大多则是口惠而实不至。(外蒙古就是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苏联强迫民国政府允许它通过“公投”获得独立的。苏联还在1941年4月13日在它跟日本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中承认了伪满洲国的合法性。——楼主点评)
与陈启修认为苏俄没有侵略中国相反,徐志摩坚决认为当时的苏俄正在侵略中国。为此他曾编发两位青年读者陈均和陈翔反驳陈启修的文章,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徐志摩对苏俄侵略的看法,陈均在反驳陈启修的文中写道:“苏俄之抛弃宣言,继续占据中东路;唆使蒙古独立;中俄会议延不举行;最近之擅捕华人……种种举动,是否不含侵略的色彩?”比陈均更进一步,陈翔则从政治、经济、文化、治外法权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苏俄对中国的侵略。“仇俄友俄”讨论的后果,徐志摩没有料想到。主张“亲俄友俄”的陈启修主持了左翼学生、工人参加的群众集会,集会之后,亲苏俄的青年学生竟然将《晨报》馆一把火烧掉。这场大火不能不引起徐志摩对苏俄的反感,原本只是观点的争论与思想的争鸣,却最终遭到亲苏俄的学生的火烧报馆,这不能不说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而这些在徐志摩看来“如饮醉酒”的中国青年所以如此,则又不能不归功于苏俄的宣传。事后,徐志摩在《灾后小言》中写道:“火烧得了木头盖的屋子,可烧不了我心头无形的信仰。”徐志摩心中无形的信仰自然是他视为至高无上的个人自由,而个人自由与以群众运动为基础的集体暴力是格格不入的。
与此同时,青年喻森的人生经历也让徐志摩对苏俄的恶感增加。喻森是一个左翼的中国青年,对苏俄充满美好的向往,于是到了莫斯科去朝圣,徐志摩在参观莫斯科时两人还见了面,相谈甚欢。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纯洁的青年,在他所热爱的苏俄没有任何自由,在他组织相关集会拥护苏俄时却遭到了苏俄军警的逮捕与羁押。原本对苏俄极度崇拜的喻森思想上不能承受现实中苏俄的种种残酷,由此成了一个精神病人,住进了苏俄的精神病院,此时跟喻森关系不错的青年人,为了让他回国,曾写信向徐志摩所在的《晨报》求助,知道了此事的徐志摩曾写文章痛斥苏俄对中国青年的戕害。
徐志摩与胡适的分歧
1926年7月,胡适游历苏俄后思想左转,开始公开宣传苏俄的成就。对此,徐志摩给胡适写信质疑胡适对苏俄的看法。作为自由主义者,对于独裁,两人都是深恶痛疾的,但胡适认为苏俄可以通过“狄克推多式”的新教育来造就一个民治政府,而徐志摩则不认同苏俄式的新教育可以造就一个民治政府。
吊诡的是,当徐志摩询问胡适看到了什么样子的苏俄式教育时,推崇苏俄新教育的胡适却没有看到新教育的内容,他所看到的是苏俄教育的统计。由此,徐志摩判定胡适被苏俄的假象蒙蔽了,而胡适之所以被蒙蔽,除了胡适呆的时间短(只三天)外,还有就是苏俄政府的刻意蒙蔽。徐志摩曾说:“苏俄之招待外国名人,往往事先预备,掩长暴短。”此前,英国历史学者威尔斯参观苏俄时,苏俄就曾通过训练学生造假来蒙蔽威尔斯。因此,在徐志摩看来,胡适所看到的苏俄,都是苏俄政府想让胡适看到的苏俄。而这种苏俄,其实是苏俄的假象。……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麻辣社区平台所有图文、视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麻辣社区平台所有图文、视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当前版块2016年12月1日之前所发主题贴不支持回复!详情请点击此处>>
当前版块2016年12月1日之前所发主题贴不支持回复!详情请点击此处>>